选择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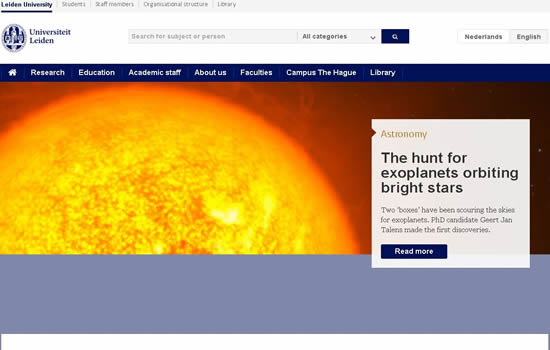 荷兰莱顿大学
荷兰莱顿大学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 巴西圣保罗大学 University of Sao Paulo, Brazil
巴西圣保罗大学 University of Sao Paulo, Brazil 台湾南华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in Taiwan
台湾南华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in Taiwan 科技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科技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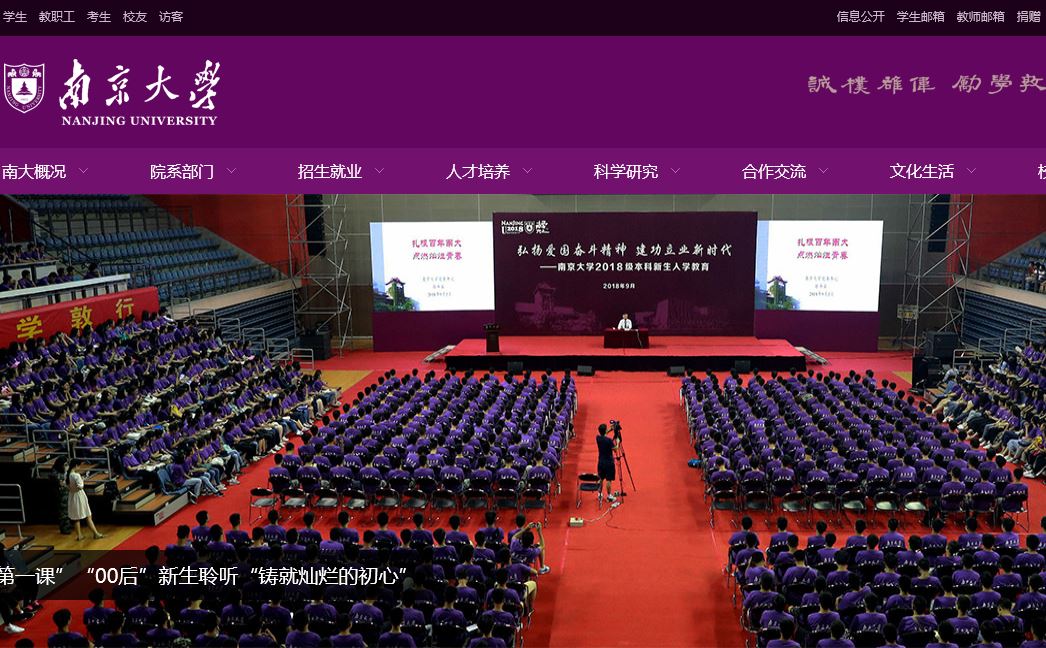 南京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上海复旦大学 Fudan University
上海复旦大学 Fudan University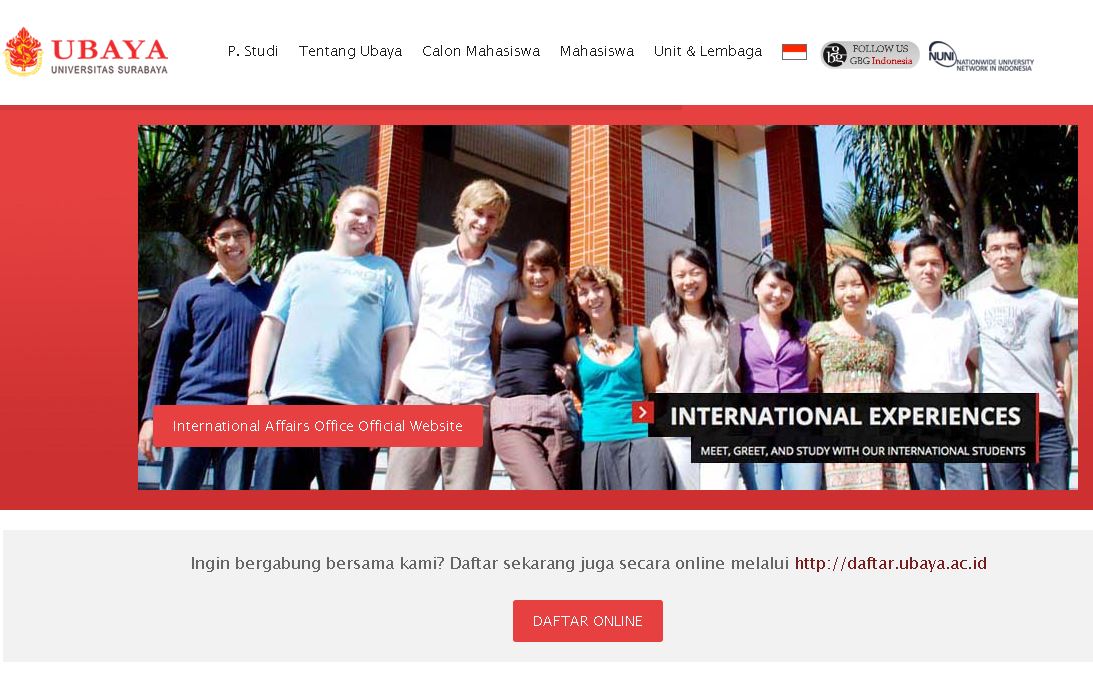 泗水大学(Ubaya)
泗水大学(Ubaya) 印尼大学 universitas indonesia
印尼大学 universitas indonesia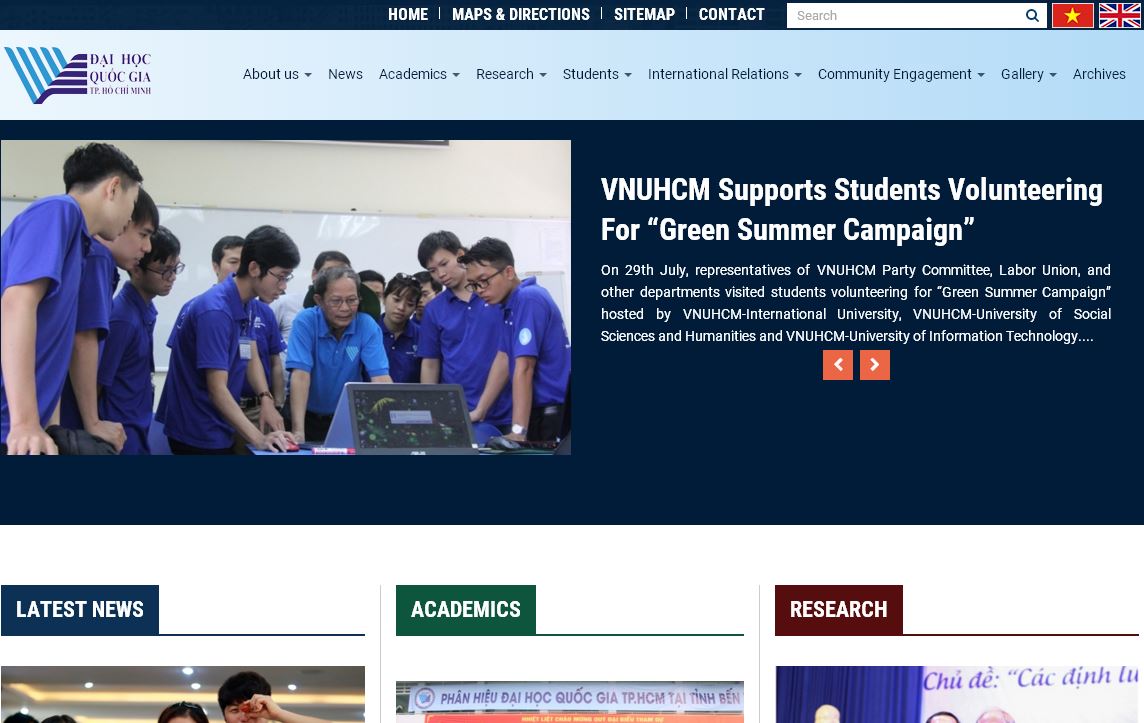 越南某大学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越南某大学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菲律宾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菲律宾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遥远的她
发布时间:2022-04-08
来源:大学网站
我尽量记录生活里的人和事儿,尽管我所触及的悲伤不如故事主角的十分之一,我把风景写成故事,把故事念成生活里的诗歌,把诗歌表达的十分之一分享给你,也分享给我。
正文:第一次去他们饭馆吃饭我就暗暗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来了。
十分简陋的餐馆就几张桌椅摆放在一边,用餐区和厨房原本是一体的,中间砌了ー堵墙隔开了,就算如此,油烟也是不住的往外冒,整个用餐区就只有一架吊扇在孤独地卖着力气。
我倒不是要嫌弃什么用餐环境,只是我坐在那里整整五分钟没人过来问我一句要吃什么,只是听到在外面的阿叔和厨房的阿姨对骂不止。
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我劝告自己不如走罢,将要起身,厨房的阿姨一身大汗,挎着一个腰包端着一碗菜,满身油腻腻的站在我面前,用着极为努力的普通话问我:你要吃什么?”语言倒是简练半点不含糊,但声调语气上倒也是显得客气十分。
看了菜牌随意点了一个继续坐下,心想算了罢,下次不来便好,一餐饭罢了随意将就将就。
坐下掏出手机,还没解锁,又听到用餐区的阿叔对着厨房骂骂咧咧起来,奇怪的是,和我一同坐着的顾客个个低头吃饭,好似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我向来就是个将就的人,最起码在对待食物上我是将就的,本着拿来主义”看到什么吃什么,所以味觉并不敏感。
大概是如此,或者是鬼使神差的,隔天中午我又来到这家餐馆,坐下依旧和上次一样没人问我点餐,但是夹杂着熟悉的对骂,奇怪的是我倒是习惯了。
因为对工作环境并不熟悉的原因,我一连好几天都来这家餐馆吃饭,倒是自己忘了第一次来的时候默默许下再也不来这家餐馆吃饭”的决心。
所谓一回生二回熟”,渐渐的我也熟悉了这家餐馆的口味,恶劣的环境,糟糕的油烟味还有他们之间的对骂。
一切都是这样的平常倒也没什么值得记录的,原本我是这样想的。
那天晚上下班忘记了时间,想到回家大概也已经过了饭点,不如在附近将就吃一顿吧,便又走到这家餐馆。
过了饭点的傍晚坐在餐馆吃饭的人并不多,除了我也只有一对母女坐在角落吃饭。
那个阿姨在门口呆呆的坐着,那个阿叔翘着二郎腿佝偻着腰在边上大口大口地吸烟,他那干瘪的身躯,看起来就像是一具干尸叼着烟一样,我赶紧移开了视线。
阿姨见我到餐馆坐下,走过来满脸笑容的问我吃些什么,态度甚是和蔼,说话间角落的那对母女吃罢饭走了,饭店阿姨憨憨地收了钱走进厨房去给我做菜。
一个人坐在餐馆里忽然间意识到好像缺少了点什么,转念一想才意识到原来是那个阿叔今天没有对着厨房里大喊大叫了。
才刚想到这,熟悉的叫喊声就又响起,那个抽烟的阿叔大口抽完一根烟后,冲着厨房叫喊了几声,便又点起一根烟走了。
厨房里面的阿姨端着我的菜冲了出来,对着阿叔远去的背影喊了几声我并不能听懂的方言,我回头望去,发现那个阿叔已经头也不回的远去。
阿姨把菜放在桌子上转身去给我盛饭,餐馆里就只剩我和她两个人,这种气氛甚是尴尬,我想我应该掏出手机转移注意力,或者随便做些什么来掩饰我的尴尬。
那个阿姨把饭放桌子上,随即和我寒暄了起来,先是她对我问长问短的,丝毫不在意侵犯我的隐私,我也不介意地一一作答了,当然我并不乐趣于谈论我的状况,说实话我还是更好奇他们之间每天对骂的是些什么。
她毫不客气地对我问长问短,倒也是给了我打探消息的胆量。
我不委婉地问她和那个阿叔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们之间说话好似吵架一般。
我怔怔的看她期望她能回答我,当然我也做好了被她回敬一句关你屁事”的准备。
谁知,我的问题使她打开了话匣子,让我这餐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
她告诉我,那个阿叔是她的丈夫。
当我听到她这样说的时候我倒也不知道是意外还是情理之中,要知道那个阿叔看起来应当已年过半百,佝偻着的腰显然是直不起来了的,那稀疏的头发近乎秃顶,我年近七十的爷爷大致看起来还要比他精神一些,而坐在我面前的这位阿姨,虽说是满身油腻腻的,一身衣着土里土气,但她的脸庞算是清秀,身上也并无多余的赘肉,甚至让我怀疑叫她阿姨是不是有些不礼貌了。
不知道她是不是看出了我内心的思考,她接着讲起了她的故事。
她和那个阿叔的确是夫妻关系并不假,她们两个一同从陕西来到深圳,现在依靠着这个小餐馆生活,她在厨房里炒菜,阿叔在前面端菜收钱顺带收拾桌子,两人分工经营这个餐馆已经三年多了。
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就是那个阿叔已经五十几岁了,而她今年刚满三十。
在他们陕西老家的时候,她的家人因为一场天灾便都去世了,唯独她一个人活了下来,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她父亲在临死前把年仅十三岁的她托付给他们的邻居,那个阿叔就是她们家的邻居。
那一年她十三岁,失去了家庭里所有的亲人,那一年那个阿叔三十几岁,究竟是三十几她说她也不记得了。
所以,你十三岁就嫁给了那个阿叔?我私自叫她丈夫阿叔”不知道是不是礼貌,但是我并不能想到更加合适的词语了。
她笑了笑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她说没有,那一年三十几岁的阿叔已经娶了老婆了,按照乡下的习俗,按理说阿叔的孩子应该比她小不了几岁,因为她告诉我十三岁那年,她父亲也不过三十二岁,但是那个阿叔一直没有孩子。
她笑着补充道,你们城里人不知道乡下其实结婚很早的。
我告诉她其实我也是乡下人。
那为什么后来?她自然是懂我的意思。
她告诉我,在乡下很看重一家的血脉继承的,因为阿叔和他之前的妻子一直没有孩子,期间吃了各种草药偏方也不得结果。
大概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她到阿叔家第二年的时候,阿叔原来的妻子就去世了,具体的原因她说她并不清楚,只是知道阿叔原来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他们娘家人在阿叔家闹了很久。
后来那个阿叔变卖了田地拿着一笔钱带着她走出了陕西到了山东。
她告诉我说,她清楚的记得那一年她十五岁,她说,那个时候她十分感激阿叔,他们家和阿叔只是邻居而已,阿叔自己在村里变卖了田地并没有多少钱财,但是依然肯带着她一路漂泊到山东。
我当然是知道的,故事远不会停留于原本那份感激的幸福时光,我能猜想到故事的发展,因此,我并不想去引出她的悲伤回忆,我只是静静的看着,眼前这个年过三十的阿姨”,她在这样一个熟悉傍晚,对着这样一个并不熟悉的陌生人,却毫不掩饰的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甚至有些害怕她讲得太多,希望她能够关上自己的话匣子,可是,似乎她并不是这样想的。
她告诉我,十五岁那年,他们就在山东一个县城里卖水果,她帮忙看摊位,阿叔搬运货物,日子过得其实也还算是好,渐渐的,生活似乎要越来越好了,十五岁的她有了自己的期待,她希望自己快点长大,或者是在十六岁那年,也或者就是十七岁那年,她希望自己能够像别的乡下的女孩子一样,早早结婚,尽管有太多乡下女孩子在十五六岁就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但是她说她并不敢奢望,她说,她那时候只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等到二十几岁了,她便有了理由不得不出嫁,她一直在等。
我依然不敢接话,毕竟她一开始就告诉我了,阿叔现在是她的丈夫,她现在三十岁是阿叔的妻子,我看阿叔在餐馆对他的态度,我不敢奢望他们是多幸福的。
她见我不说话,也沉思了许久没说话,我们安静的坐着,我吃饭都不敢发出声响,矫情的说,我好怕打扰了她。
但毕竟,我还是打扰了她。
她见我碗里的饭吃完了便起身给我盛饭。
我一声不响。
后来,你知道的”她说道。
她告诉我,她清楚的记得,那年她十七岁,那年他们的水果档被别人砸掉了,几个男人带着铁棍到他们水果档那里砸完便走。
几乎和所有能够猜到的故事一样,因为水果档的经营赚了点钱,从乡下出来的阿叔过了太久乡下那种无聊的生活,在城里染上赌博的恶习。
我并不是对乡下生活有什么偏见,但是,依照我自己在贫穷的乡下生活了那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在贫穷的乡下,男性多半是有赌博的恶习的。
她的话也证实了我的猜测,因为恶赌,他们的水果档被砸掉了,十七岁的她那年独自面对了数不清次数的催债。
就在一个星期后,阿叔回到了他们的住地,带着她一起跑到了哈尔滨。
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十年。
所以,你是就是在哈尔滨嫁给了阿叔吗?我斗胆问了这一句,说罢我又陷入了无限的懊悔当中,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冒失的举动是否会打扰到她,不过,显然我是多虑了。
她近乎讽刺的笑了一声,说道:也可以这样说吧”。
我没有接话,我已经冒失的问了不该问的问题了,她的反应告诉我,我刚刚的行为显然是不礼貌的。
她停顿一会儿,接着说起了哈尔滨生活的那十年生活。
她告诉我,她十分清楚的记得,那一年她依然是十七岁,那一年虽然水果档被砸了,虽然他们又一次远走他乡,但是,她依然感激一路都带着她的阿叔。
她叹了口气告诉我,自从到了哈尔滨的那个晚上,一切就都变了。
哈尔滨火车站的夜晚是灯火通明的,那天晚上下着雪,虽然火车站已经有些破旧了,但是漫天的白雪让这座城市显得格外的白净,白净得就像是十七岁的她一样。
天气太寒冷了,虽然在山东他们穿着厚厚的衣服,但是下了火车来到这冰天雪地了她还是感觉太冷了。
在夏天的深圳,在她破旧的小餐馆里,我吃着饭,吹着呼呼的风扇,她在边上的桌子坐着,告诉我说,她记得那一年是怎样的冷,她说她应该忘记不了那种感觉。
那个三十几岁的阿叔看到她瑟瑟发抖的站在火车站前,一把将她搂到怀里,她感觉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还有一个熟悉的人,一个不怎么样强大的臂弯,但至少她感觉到有些依靠,从陕西的乡下到山东的城市里,从山东的城市里到哈尔滨火车站前,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失去父母家人的少女,离开家乡和朋友,和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一同站在火车站人来人往的街口,她不用告诉我,我也懂得那种感受。
那天晚上,他们在火车站附近一个破烂的旅社住下,就是那一晚她成为了阿叔的妻子,不管她承不承认,事实已然成为事实,说到这里她似乎呆住了,不往下说了。
我也停了很久没说话,看着她的脸,我知道岁月已经过去,三十几岁的她现在已然老去,甚至比她应有的年纪还要老一些,我很难透过她现在的模样去想象她十七岁少女时期的模样,但是,我读过些书,看过些电影,我也见过许多十七岁的小女孩,走在路上看到那些穿着校服的女孩子,无论她模样如何,我总是能确定的是,青春是一个女生最美的时期。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莫名其妙的联想到这些,但是当我想到一个十七的少女被一个三十几的老男人拥入怀里,在一个陌生城市的火车站旅社里,女孩也许是哭丧着脸,也许是叫喊着,也许是挣扎或者是沉默不语,但是不管如何,她是终究是接受了这已经发生的一切,这种莫名其妙的画面感让我感觉到忧伤。
你有烟吗?”她问我。
我怔了一下,有些恍惚,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她,但是我都没有开口,停了一会儿,我拿出一支烟给她点上,她深吸一口,随后叹了长长的一口气,烟雾在傍晚时分的落日下竟然显得格外有诗意。
你不愿意听这些吧?她又一次打破了我们尴尬的气氛。
所以你在哈尔滨生活了十年是吗?我故意回避她的问题,我希望把话题转移到轻松愉快的话题上。
她思考了一会儿说到:其实告诉你也没关系,反正也都过去了。
第一天晚上在哈尔滨的经历让她再一次感觉到生活的刺痛,上一次那种难受的感觉是在她一夜间失去父母家人的那一次,这一次,她失去了她自己,但是她反而感觉有些轻松,从十四岁到十七岁这三年间,她感觉到自己欠那个阿叔的太多太多,原本那个阿叔在陕西乡下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也算是幸福,除了没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以外,家庭和睦生活算是滋润吧,最起码在她看来是这样的。
可是自从她到了他们家里,阿叔的老婆死去了,离开了原本生活了三十几年的陕西乡下,到了山东,颠沛流离又到了哈尔滨,善良的乡村女孩听了太多扫把星”的说法,虽然她也是这不幸生活的受害者,但是她把全部的不幸揽到自己的身上,她觉得这所有的不幸都是她带给那个阿叔的。
因此,阿叔强暴她的那一晚上,她感到不幸生活的沉重,同时她也感觉到释然,她还清了她的债,她用一个十七岁少女的贞洁偿还给这个被她拖累”的男人。
她一夜没有睡觉,她想到在山东那家水果店时候她的梦想,一个女孩青涩的梦想,她也想要嫁一个结实的汉子,她可以给他洗衣做饭,甚至和他一同下地干活,然后给他生个宝宝,安稳的在城里或者是在乡下生活,为了柴米油盐而争吵,为了鸡毛蒜皮而争吵,但是,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会有自己邻居,会有自己的孩子,偶尔也站在街口和其他长舌妇一样说长骂短,但是终究会有自己的生活。
这样平凡的梦想,让她那一夜流光了泪水,她意识到,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她还能等待自己慢慢长大,然后顺理成章的过自己的生活,可是,她知道,那晚上以后都变了。
她的梦想破碎了,她知道这一切都成为了不可能,她不恨那个阿叔,那是欠他的,她要还的,早晚都是一样,早点还了甚至说不上是开心还是难过。
可是,她恨那些到她水果店里去砸她们摊位的那些男人,是那些人把他们逼迫到这个陌生的哈尔滨,如果不是他们,那天晚上的一切也都不会发生,她也不会丢失自己,也不会丢失梦想。
她知道,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她只能离开这里,离开现在的生活,她要依靠自己,而不是那个阿叔。
反正现在她还清了她的债,她要离开。
我听她的故事到这里,我泛起一阵不知是同情还是敬佩的复杂情绪。
我想起曾经我读过萧红的作品,她同样是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她为了逃离桎梏一般的爱情生活选择离开,她想要到北平去,那时候的北平对她而言不正是梦想的圣地吗?我知道,对于那年十七岁的她,只要没有那个阿叔在的城市,都是她的圣地。
所以,你离开了哈尔滨吗?我问道。
她没有离开哈尔滨,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她在讲故事前就已经告诉过我,她在哈尔滨生活了十年。
毫无疑问,我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但是我知道,这个问题其实是我内心最想得到解答的问题。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就起来了,我想要偷偷的跑出去,我身上没有一分钱,但是我知道,我要跑出去。
可惜,我没能成功。
”她望着远处,手上夹着那根快烧完的烟,慢慢的说道。
她还是被发现了,那个阿叔在她开门的时候醒来,把她绑在床上,她不吃不喝呆了三天,最后,她屈服了。
当她三天后咽下第一口饭的时候,她就接受了生活里发生的一切。
这三天里,她含泪咬牙接受了那个阿叔一遍又一遍对她所做的一切,她甚至没有喊,也没有挣扎。
她讲得十分冷静,没有半点波澜,我看到她手上的烟烧完了,马上要烫手了。
我不敢想象她所讲的画面。
不记得在什么时候,我读过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那时候,当我读到小说顾曼桢被她姐夫关在那栋楼里所强暴的时候,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我时常在读到类似悲伤情节的时候不能够继续读下去,要放下书本,歇息许久,然而,这次我却听着这个活生生的人坐在我前面讲着比书本上还要悲惨的故事,我知道,这不是书,我无法放下。
我不想继续听她的故事了,我意识到这餐饭我吃得太久太久,久到令我悲伤。
她看到我一言不发的坐着,手里端着那半碗饭怔怔的坐着,她问我怎么了。
我想了想不知道撒什么谎好,于是,我把《半生缘》里顾曼桢的故事告诉她。
她饶有兴趣的看着我听我说故事,当我讲到顾曼桢被她姐姐骗到家里那段的时候,我看到她那双眼睛里止不住的掉泪水。
我坐在她对面,隔着不远,看到一个三十岁的女人的眼泪,实在分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她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不知道她还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她先前的故事已经足够悲伤了,这个可怜的女人,在讲述自己的过往十几年的悲伤的故事时都不曾掉下半点眼泪,可是在听我讲完一个小说上的故事时,眼泪却如决堤一般。
我不知所措的坐着,静默地看着她。
我甚至忘记要给她递一张纸巾,她歪头在自己的衣服上擦了擦眼泪,尴尬的笑了。
她一笑我也只好勉强的跟着微笑。
我告诉她我讲的就是一个小说上的故事而已,小说多半是虚构的。
她又哭又笑的说着:那就好,那就好。
在哈尔滨那十年其实她受了很多苦。
在哈尔滨生活的前几年,她被那个阿叔关在屋子里,那个阿叔去工地打工,早出晚归,她就一直被锁在屋子里面,用绳子绑着,什么也做不了,她开始恨那个阿叔,她不甘心就这样过日子,她说她用了各种方式想要逃跑,每一次都被抓回去,那个阿叔白天在工地打工,晚上回去发现她想要逃跑迹象就暴打她一次,那个阿叔也变得不像以前了,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后来她假装屈服了,终于跑出去了,在街头游荡了一个多月,她想要回去陕西的乡下,可是,她身无分文,甚至连证明自己身份的方式都没有。
她成了街上那种流浪者。
她甚至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她没有勇气。
我看着她,她脸上没有表情,说这些也像在说别人故事一般,异常平静,我显得比她都要难过一些。
后来,她躺在一个垃圾堆边上,她连动都不想动,她想不如就这样安静的饿死吧。
在垃圾堆边上过了三天三夜,直到有一天晚上,有一个男人路过那个垃圾场,把她救回了家。
后来的故事,她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并没有仔细说,但是,我能想象那些不幸的画面。
她在哈尔滨附近的乡村里,被这个老男人蹂躏了一次又一次,最终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不过,四年后这个孩子死去了。
孩子死去的那天晚上,她又从乡下跑回了哈尔滨,又找到了那个带着她来到哈尔滨的阿叔。
一方面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她又要选择回去哈尔滨那个阿叔家里,另一方面,其实我懂的,在两个不幸的遭遇前,很显然,前一个阿叔对她而言,最起码还有一丝丝亲人的含义。
后来的几年里,她屈服了,成为了阿叔的老婆,和他一同在哈尔滨生活了下来,又做起了小本买卖,过了几年,她和那个阿叔一起离开了哈尔滨,来到了深圳,在现在他们的饭馆这里,做起了生意。
她在那个改造的狭小的厨房里做饭,那个阿叔在前面端菜送茶。
她在讲她的故事的时候,大致讲了许多她在陕西乡下的生活,和她在山东卖水果的那段时间,至于她后来在哈尔滨和深圳的生活,她只是了了带过。
我猜想,对于她而言,过去不幸的生活,她最怀念的应该还是在乡下和在山东卖水果的日子,只可惜,遥远的她,再也回不去了。
在以前我常常写一些悲惨的小故事,我依然记得,我曾经写过一个悲惨的故事,讲住在城市里的初中生因为不幸的遭遇被一个老男人强暴的故事。
当时我的朋友说我太残忍,说我不懂贞洁对于一个女孩的重要性,那时候我不懂。
当我听完这个三十岁女人的故事时,我知道,我们常说一个人的人生可以自己掌握,然而,她的故事却在嘲讽我们太过乐观了。
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他们的小饭馆吃饭,我也许并不是怕下一次面对时候的尴尬,而是我实在说服不了自己再去面对那个悲伤的故事。
【遥远的她查看网站:遥远的她】
- 上一篇: 一朋友和他男票过四周年纪念日
- 下一篇: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并没有留下太多印象
相关阅读
目录列表
资讯列表
大学选择
随机选择
校园资讯
- 热点
- 网站
- 新收



共0条评论
网友评论温馨提示:您的评论需要经过审核才能显示,请文明发言!